深冬的风是淬了冰的针,尖啸着扎进衣领、钻进骨髓,连呼出的热气都在半空中凝成细碎的冰晶。天地间是一片凝固的白,雪层厚得像裹了层绒被,把街市的喧嚣、行人的踪迹全捂了进去。唯有树梢垂着的冰凌,在日光下折射出棱面,晃得人眼晕。
羽绒服的绒毛被风灌得发硬,路人把围巾又紧了紧,还是挡不住那股从鞋底往上钻的寒气。街上的人都缩成一团,脚步匆匆,像被风赶着往暖处钻。可这凛冽里偏有种干净的美——雪粒打在睫毛上,冰棱垂在屋檐下,让人忍不住停下脚步,看这天地被冻得透亮的样子。
空旷的长街上,那个邋遢的身影走得很慢。
他的棉衣沾满了灰渍,下摆磨出了毛边,头发结成一缕缕污黑的绳,糊在冻得发紫的额头上。脚下是双露出脚趾的破布鞋,踩在雪里,每一步都留下个湿冷的印子。他走得歪歪扭扭,像被风揉着晃,却偏要把腰杆挺得很直,哪怕手已经冻得蜷成了鸡爪。
路过的店铺飘着热包子的香气,他的喉结滚了滚,却只是把脸别向一边。没人停下脚步,更没人递来零钱,只有个挎着皮包的男人嫌挡路,狠狠撞了他一下,嘴里骂道:“死疯子,挡道!”
他踉跄着稳住身子,指节抠进冻硬的棉衣布料里,指甲缝里渗出血丝。眼睛瞬间瞪得通红,像被踩了尾巴的兽,喉咙里挤出破碎的嘶吼:“滚!别碰我!”
男人骂骂咧咧地走远,皮靴碾过冰碴的脆响,混着风的尖啸,在空荡的长街上飘了很远。他盯着那道消失在街角的背影,喉结滚了滚,最终还是把到了嘴边的咒骂咽了回去,只剩雪粒落在睫毛上,凉得让他打了个哆嗦。
风掀动他的衣角,雪粒沾湿他的发梢,他一边走一边踢着脚边的雪块,把蓬松的雪踢得四散飞溅。嘴里始终念念叨叨,声音又哑又碎:
“这个世界怎么会这样……不公平,一切都不公平……”
“怪你们,都怪你们……都是你们害的!”
他的话东一句西一句,像是在跟空气吵架,又像是在对着虚空质问。路人纷纷绕开他,连眼神都吝于施舍,仿佛多看一眼都会沾染上晦气。他浑不在意,只顾着往前走,脚步踉跄却不肯停。
影子被拉得又瘦又长,和他身上的脏污一起,在雪地上拖出一道歪扭的痕。他的目光始终落在前方——那片被雪光映得发白的远方,像在等着什么,又像在找着什么。或许是一个能让他停下咒骂的答案,或许是一场能烧尽这寒意的火。
他脑子里的声音像无数只尖利的虫,正啃咬着他的骨血。
“你生来就是这样的命!”
“这么多年了,你还是没本事啊颜平安!”
“都二十七了,连个媳妇都讨不到!”
“你就注定是打工的命,别想着飞上枝头变凤凰!”
那些声音不是从耳边传来,而是直接从他的五脏六腑里钻出来的,像附骨之疽,每一句都在他的神经上狠狠拉扯。他能“看见”那些人影——是父母佝偻的背影,是工友戏谑的嘴脸,是相亲对象鄙夷的眼神,它们都变成了活在他脑子里的寄生者,盘踞在他的意识深处,把他所有的不甘和念想都啃得稀碎。
“不!我不甘心!”
他在喉咙里发出野兽似的低吼,声音嘶哑得像破锣,“我不想一辈子给人打工!要不是你们把我踩在泥里,我怎么会沦落到今天!”
绝望、愤怒、不甘像滚烫的岩浆,在他胸腔里翻涌,却找不到一个出口,只能把他的五脏六腑都烧得发疼。他觉得自己像被扔在冰水里,周围的寒冷都比不上心底的凉。那些声音还在继续,像针一样扎着他的太阳穴,每一次搏动都让他眼前发黑。他想嘶吼,想把这些声音都撕碎,可他只能在雪地里踉跄着,像个被抽走了骨头的木偶。
他一边走一边笑,笑声又干又哑,像生锈的铁片在互相摩擦。那笑声里全是疯癫,全是对这可笑世界的嘲弄,更全是压得他喘不过气的无奈——他像一粒被狂风卷着的雪,明明想往温暖的地方落,却只能被命运摔在冰冷的泥里,连挣扎的力气都没有。
他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拖进了意识的深渊,那些黑色人影从四面八方涌来,像潮水般将他彻底淹没。它们没有脸,只有模糊的轮廓,却每一个都带着熟悉的恶意——父母的叹息、工友的嘲讽、路人的鄙夷,全都凝聚在这些黑影里,像冰冷的锁链缠上他的四肢。
他想挣扎,想嘶吼,可喉咙里只能发出细碎的气音。黑影越挤越近,像黏稠的墨汁糊住了他的口鼻,连呼吸都带着铁锈般的腥甜。那些声音也跟着沉了下来,不再是尖刻的咒骂,而是变成了嗡嗡的蜂鸣,钻进他的头骨,啃咬着他的神经。
他感觉自己正在融化,像雪粒掉进滚烫的铁锅里,连骨头都要被熬成一滩烂泥。意识彻底沉了下去,只剩下无边无际的黑暗,和那些永远散不去的黑影,在他脑海里反复碾过他仅存的一点念想。
他就这么沿着公路往前走,不知道走了多久。
白天靠捡垃圾桶里的剩饭剩菜果腹,夜晚蜷缩在桥洞或者废弃的砖窑里,听着风卷着雪粒拍打在铁皮上的声响。有时候走累了,就坐在路边的雪堆上歇一会儿,看着来往的车辆卷起细碎的雪雾,没人会多看他一眼,更没人会问一句“你要去哪儿”。他像一粒被风裹挟的浮尘,在天地间漫无目的地飘荡,连自己都不知道终点在何方。
鞋底的破洞越来越大,脚趾冻得失去了知觉,棉衣上的灰渍也厚得像一层壳。直到某天清晨,他翻过一道山梁,远远看见山坳里卧着一片黛瓦白墙的屋舍,炊烟正从屋顶袅袅升起。他犹豫了一下,还是拖着灌了铅的腿,一步步朝着那片烟火气挪去。
在那黔州的偏僻小镇上,没人知道他叫什么名字,这里的人都叫他“疯子”,这里的人似乎都习惯了这个身影的出现。自从这个邋遢的人来到这个小镇后大街小巷看不到一点垃圾。
他总是天不亮就醒,揣着捡来的破麻袋,沿街把果皮、纸屑、烟蒂都扫进袋里,连墙角的蛛网都要伸手扯干净。镇上的人起初还躲着他,后来见他除了念念叨叨从不伤人,反倒把街面打理得比镇长雇的清洁工还利落,便也渐渐放下戒心。卖包子的阿婆偶尔会把刚蒸好的菜包塞给他,他却总梗着脖子摆手,直到阿婆板起脸说“再不吃就喂狗了”,才会红着脸接过来,蹲在墙根下,一口热包子就一口雪,吃得眼睛发亮。
在那脑海深处这里就像是一个平行世界一般,这里没有那外界的车水马龙,没有那高楼大厦,没有那外界的两班倒的生活。他彻底忘记了所有的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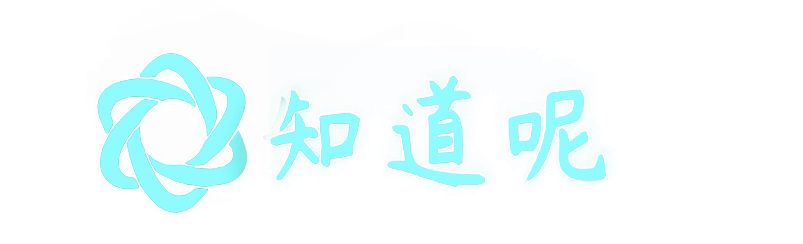



还没有评论,来说两句吧...